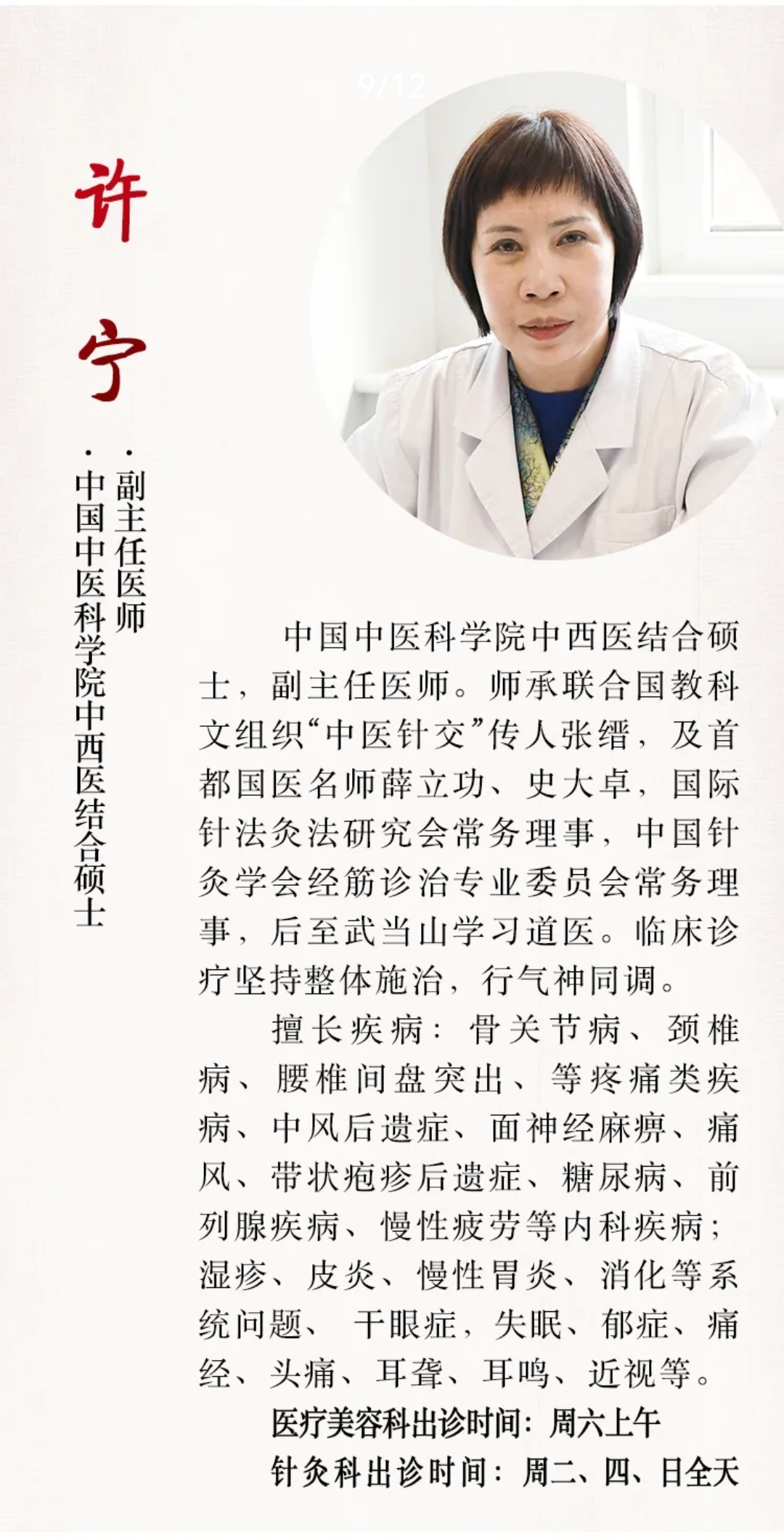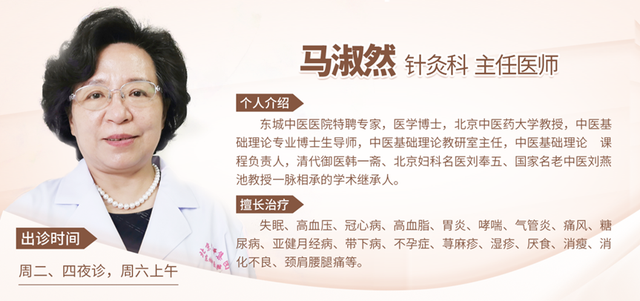成为女人,忘记女人:在性别观念的鸿沟中写文学可以吗?
如果你把《你自己的房间》作为宣言和女性写作指南,你肯定会和弗吉尼亚·伍尔夫一起经历大脑分裂。”赚钱,写作,生活!”在听了伍尔夫关于女性写作的困难和未来的演讲后,这种鼓励被成功地完成了。但谁能料到,她的话变了,给了我们一个打击:“女人关心一点委屈,无缘无故地呼吁任何利益,说话多少像女人一样,这是致命的。”
“她像女人一样写作,同时又忘了自己是女人。”“一个人怎么能成为伍尔夫作品中的简·奥斯汀,像女人一样写作,却忘了做女人?简·奥斯汀真的处于这种写作状态吗?她忘了什么,记得什么?像伍尔夫这样深知父权社会压迫的女性,怎么能在写作中忘却愤怒?毕竟,伍尔夫本人似乎做不到。

问题不止于此:如果你放弃愤怒所代表的情感,你是否也失去了其中包含的女性经验?女性作家要想抛开狭隘、偏颇的性别意识,需要经历怎样的自我割裂?为什么一些女作家在谈到性别问题时,对自己的女性立场坚定,但在写作时却总是警惕自己的性别意识,甚至怀疑自己的女性身份?
本文希望通过借鉴英国作家弗吉尼亚·伍尔夫、美国科幻作家乔安娜·拉斯和意大利作家埃琳娜·费兰特的思想,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。同时,借助中国文学研究者张黎的研究和调查,我们可以把这些问题与中国当代写作的现状联系起来。女性意识的觉醒建构了一个属于女性的文学空间。即使父权制仍试图将其拆散,传统已经形成,更大的危险来自内心。作为反思视角,性别意识在拆解过去的文学作品时也在撕裂自己,这是一场不断建构与拆除、记录与改造的游戏,男性往往觉得你不需要参与其中。

《我的房间》:女性写作传统的建构与危机每个女性作家都必须面对这个问题,她们的读者也不例外。只要对文学史有一点了解,男女都不禁产生这种怀疑。毕竟,男性作家的伟大作品摆满了整个书架,简·奥斯汀和艾米丽·勃朗特就夹在其中,安静而瘦弱。即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文主义者乔治·施泰纳也不得不问:“为什么女人不能创造更多的东西?”
两位20世纪的女作家曾经回答过这个问题。一个是安吉拉·卡特,她的回答非常直截了当:“世界上只有一个莎士比亚,该死的。”另一个是弗吉尼亚·伍尔夫,他的回答也非常简单明了:“莎士比亚的天才不会出现在勤劳和不识字的人中间。”在16世纪的英国,妇女年轻时几乎不得不承担家务。他们的父母认为这是正常和美德。读书是不必要的、可耻的爱好。小女孩几乎没有闲暇时间。他们的生活围绕着修补、清洁和繁殖。不仅是普通人,贵族夫人温切斯也在她的诗中表达了她对女性处境的不满:“有人说像奴隶一样做无聊的家务是我们最高的艺术和最大的用处。”伍尔夫假设,如果莎士比亚有一个和他一样有才华的姐姐朱迪思,只有当她看到她哥哥的才华展示出来时,她才会自杀,死后被埋葬在十字路口。因为她父母好心地让她尽到自己的职责,剧院经理会像开玩笑一样把她拒之门外,她也无处可去,在街上徘徊,也许是一位善良的绅士,我会收留她,等她怀孕后离开她。

伍尔夫认为,如果16世纪的女性有天赋,她们就会发疯,要么自杀,要么隐居。周围的环境千方百计阻止他们写作。这种压迫被内化到他们的身体里,成为匿名的本能。即使有些残存的人才可以通过诗歌和故事的形式传播,人们也不知道作者的名字。即使在19世纪,玛丽·安·埃文斯也只能躲在“乔治·艾略特”的外衣下躲避麻烦。艾米莉·勃朗特的身份曝光后,备受赞誉的《呼啸山庄》成了“一个彻头彻尾的怪物”。经过18世纪末的女权运动和19世纪的工业发展,女性开始控制自己的钱包。中产阶级妇女能够通过笔头和大脑知识挣钱。虽然收人不多,但他们不必依靠父亲、兄弟和丈夫生活。《傲慢与偏见》、《简爱》和《维多利亚》在传统的缺失下,为后来者树立了良好的榜样。到了20世纪,已婚妇女不能拥有自己财产的障碍已经扫清,更多的职业向妇女开放。于是,伍尔夫对剑桥大学高尔顿学院和纽汉学院的女学生说:是时候省下500英镑的年金和自己的房间了,为朱迪思的复活而努力,把女诗人不朽的灵魂带回人间。
毫无疑问,文学史上受益于妇女解放运动的女作家越来越多,这些女作家也可以看作是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。他们用钢笔为自己的性别争取一席之地。在中国,妇女解放与妇女写作的关系可能更为密切。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在《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》一书中指出,中国现代女作家的诞生缘于两场战争:“一场是‘贤妻良母’的解放妇女的战争,另一个是五四时期的“超级贤妻良母”战争,“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把家里的妇女视为国家贫困的原因之一,主张妇女走出家门,成为健康的公民。学校教育为女学生提供了一张“安静的书桌”。他们不再需要被困在家务劳动中,有时间坐下来静静地思考。到了五四运动,一个大写的“人”字被高度宣传。妇女解放从集体生产力的提高走向个人人格的发现。妇女的价值并不取决于她是谁的女儿、谁的妻子和谁的母亲。”“人类”是唯一的确认。一批女性经历了闺蜜女、女学生、女市民、人的身份转换,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冰心、鲁音,后来还有丁玲、萧红、张爱玲。
《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一代》张莉著,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2020-2009,在国内外确立了20世纪相当可观的女性写作传统。最初的几块石碑矗立在荒原上,凝视着辉煌的人类宫殿。现在他们照顾自己的世界,这个世界也许并不那么丰富,但这足以为后来者提供一个不受干扰的空间,一堵墙就能找到适合自己经历的文字和书籍。他们有的自觉地用女性主义的视角来批判对女性作家的压抑,思考自己的写作实践,有的则在文本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不同于男性的性别意识,从而被纳入“女性解放”的讨论之中,“什么是女性写作”或“什么是女性意识”
拉尔斯在《如何抑制女性写作》一书中写道:“年轻女性失去了她们的榜样。”事情不像伍尔夫想的那么乐观。朱迪思一百年后就会回来。文学史上可供检索的女性姓名更多,官方的认可来自这些碑文。回顾我们所接受的正规教育,中小学必读书目仍然停留在19世纪的几位女作家身上。年轻女性要想接触到多丽丝·莱辛、玛格丽特·阿特伍德、托尼·莫里森等作家,就要努力探索,但所有优秀的读者都能隐约看到俄罗斯男性作家的继承与发展。妇女形成了自己的传统,但她们不断被打破和分离。他们没有母亲,没有女儿,孤身一人。每一代的读者,每一个女人,都要四处收集砖石,重建被风暴摧毁的房间。